让·齐格勒:瑞士资本家们的”头号公敌“

在巴黎经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伏娃的引导,他对政治日渐沉迷;切·格瓦拉则给予他职业规划建议。社会学教授让·齐格勒(Jean Ziegler)无疑是对资本主义以及瑞士商业行为最尖锐犀利的批评者之一。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特此对其进行了专访。
让·齐格勒(Jean Ziegler),现年88岁高龄,业已退休的社会学教授,他曾是世界上针对全球化最富盛名的抨击者之一。卸甲归田之前,他曾在日内瓦大学担任教授,并于1967年至1999年期间作为瑞士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代表在瑞士联邦议会担任议员(期间有4年间隔),同时,他也是联合国食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目前,他仍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成员。
齐格勒执笔写过多部畅销书籍,但他本人也因与利比亚前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oammer Gaddafi)和曾掌权津巴布韦37年之久的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交往而屡遭诟病。现如今,他与妻子定居在日内瓦州境内的鲁桑镇(Russin)
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你被视为瑞士最辛辣犀利的批评家之一。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如今的你?
让·齐格勒: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一段虽无忧无虑,却古板狭隘、目光短浅的童年生活。尽管如此,每当我目睹贫穷的人或事,我都会为之感到震惊。可我的父亲总是说:“这都是上帝的刻意安排。”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宿命”。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让人无法忍受。
后来在巴黎,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伏娃最终递给我理解世界和力争改变的工具。多亏了他们,从那时起,书籍才日渐成为我对抗的武器。
切·格瓦拉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在我的抗争中,切可以说是一位“战略制定师”:他帮助我进行了颠覆性的整合。目的是要渗透到各个机构中去,从而利用它们的力量来达成我要实现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力争成为大学教授、议员、甚至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你曾于1967年至1999年期间在瑞士联邦议会担任议员,并因1989年短短一年之内相继呈交了38份立法提案而赢得各方赞誉。步入政界,是否有助于你推动变革?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瑞士议会实质上并不拥有什么实际权力。实际上,身为一名议员,你能获得的报酬相当微薄,所以一旦你当选议员-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得隶属于持右翼立场的党派,你就会很自然地得到譬如雀巢、罗氏、瑞银和瑞信等知名企业董事会的职位,身处其中的你就可以拿到数十万瑞郎的高薪。通过这种途径,你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名唯利是图的利益集团“雇佣兵”。
举个简单的例子:彼时,鉴于瑞士相关金融法律并不适用于律师在该国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情况,因此,经合组织当时正致力于敦促瑞士对相关法规进行调整,针对洗钱行为作出严化处理。面对经合组织施加的压力,瑞士政府提出了反洗钱法提案。然而就在去年9月,瑞士联邦议会却驳回了这一提案。毕竟,银行寡头总是占据多数席位的。

在世人眼里,你是应该对废除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负主要责任的推手之一。
瑞士银行业保密制度并没有消亡。强盗银行还继续存活着。类似“瑞信机密”(译者注:由国际反贪腐组织“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组织协调发起的调查,该调查发现了数十个存在问题的账户,资产总额超过了80亿美元,账户持有者为腐败官员、人权侵犯者以及涉及贩毒、洗钱、和其他严重犯罪活动的关键人物)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丑闻显示,一切照旧。尽管如此,现如今,银行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正使得投机者们的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他们被曝光于天下是早晚的事。
你的著作总能引起轩然大波。你最著名的书籍之一-于1990年出版的《瑞士的自我粉饰》(Die Schweiz wäscht sich weisser),当年面世之时就像是在瑞士国内投掷下一颗炸弹。其后,你连续九次面临银行、律师、甚至是独裁者的起诉。最终,你失去了一切,也包括你当时在瑞士议会的席位。
当时我的确受到了多方威胁,甚至还屡次接到过匿名电话。据新闻界报道,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隐匿的金融黑手操纵着我撰写了那些故事。还有一些疯狂、精神错乱的人坚信,我是导致他们离婚的始作俑者。因此,我不得不在警察的保护下生活了整整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的家人也同样承受了很多痛苦。但我丝毫不抱怨:毕竟,我为此享受到了特别待遇。
面临所有的指控,我均已败诉告终。那本书九个翻译版本中的每一版,都被当成一起独立的罪行处理。但我暗自思忖,这或许也是一个利用法庭来进行抗争的良机-因为银行家们必须站在法庭上,公开一一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
但后果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在大学里的工资被悉数没收了。我只能依靠最低限额的工资聊以谋生。我靠着出版书籍赚来的所有收入,都被查封了。现在你看到的这所房子,是属于我妻子的。当时我们夫妇俩还能来得及保留一些东西,但现如今连我的车都是租来的。

你如何看待瑞士政治制度的特质-直接民主呢?
在我看来,直接民主是一件好事,但在我们这么一个并不平等的社会里-要知道,仅占我们国家人口数量2%的资本家,却掌控着逾半数的瑞士国民整体财富-那些有钱人让绝大多数人对其屈服。对于每一项涉及立法提案所提出的公民动议,那些期盼着选民们不假思索就作出反驳的人,传播的论点往往都是:该提案一旦通过,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国家开支增加。在他们宣传的威慑下,选民们会投出与自身利益背道而驰的选票:反对五周带薪假期;反对同一标准的医疗保险缴费-虽然提案会让人均保险费用降低30%;反对提高公共养老金。
尽管如此,你依然与瑞士最声名显赫的资本家代表人物之一-业已卸任的雀巢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包必达(Peter Brabeck)进行了一系列对话。
我的政治斗争历程始终深受萨特的一句话的启发和鼓舞:为了真正地爱民众,一个人强烈憎恨的,必须是那些压迫他的东西,而不是压迫他的个人。如果包必达无法让他所掌舵的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那他自然就无法再胜任雀巢集团的总裁一职。他本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那些跨国集团才是症结所在。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跨国公司500强共同控制了全球范围内国民生产总值的52.8%。它们只痴迷于唯一的战略: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利润最大化。
然而在中国,资本主义使得该国8亿人在过去短短40年间-尤其是邓小平于上个世纪70年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之后-就摆脱了贫困。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效率的实证吗?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活力及最富创造力的,但它也是单一民族国家或者会社、联盟所无法把控的。企业往往拥有着国王或教皇都不敢奢求的至高权力。而这最终会导致一个同类相残、人类自相残杀的世界秩序。眼下,我们都在对抗饥饿。我们都在与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毫无限度的权利进行斗争。我们都在与全球变暖作战。
资本主义对于全球变暖也负有一定责任吗?
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任何公共权力机构或政府当局能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独立执行《巴黎协定》框架下由各参与国达成共识的规范。因此,对地球造成的破坏,是资本主义直接酿成的恶果。我们不妨以2015年缔结的《巴黎协定》为例。该协定旨在将全球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相比高出1.5摄氏度以内。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2022年,石油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于利润丰厚的原因还增加了两倍。
你如何看待世界各国首都以“星期五为未来而战”运动(Fridays for Future)的名义走上街头参与抗议示威活动的年轻人?
对我来说,这无异于是历史的奇迹。这种倏然间某种意识觉悟的迸发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星球。这种令人惊异的运动风潮-一种思想意识的叛乱,是突然之间就出现的。它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意味着年轻群体开始思考跨国公司的辐射力。他们亲眼见证了跨国公司带来的满目疮痍、风暴、沙漠、饥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译自英文:张樱)

符合JTI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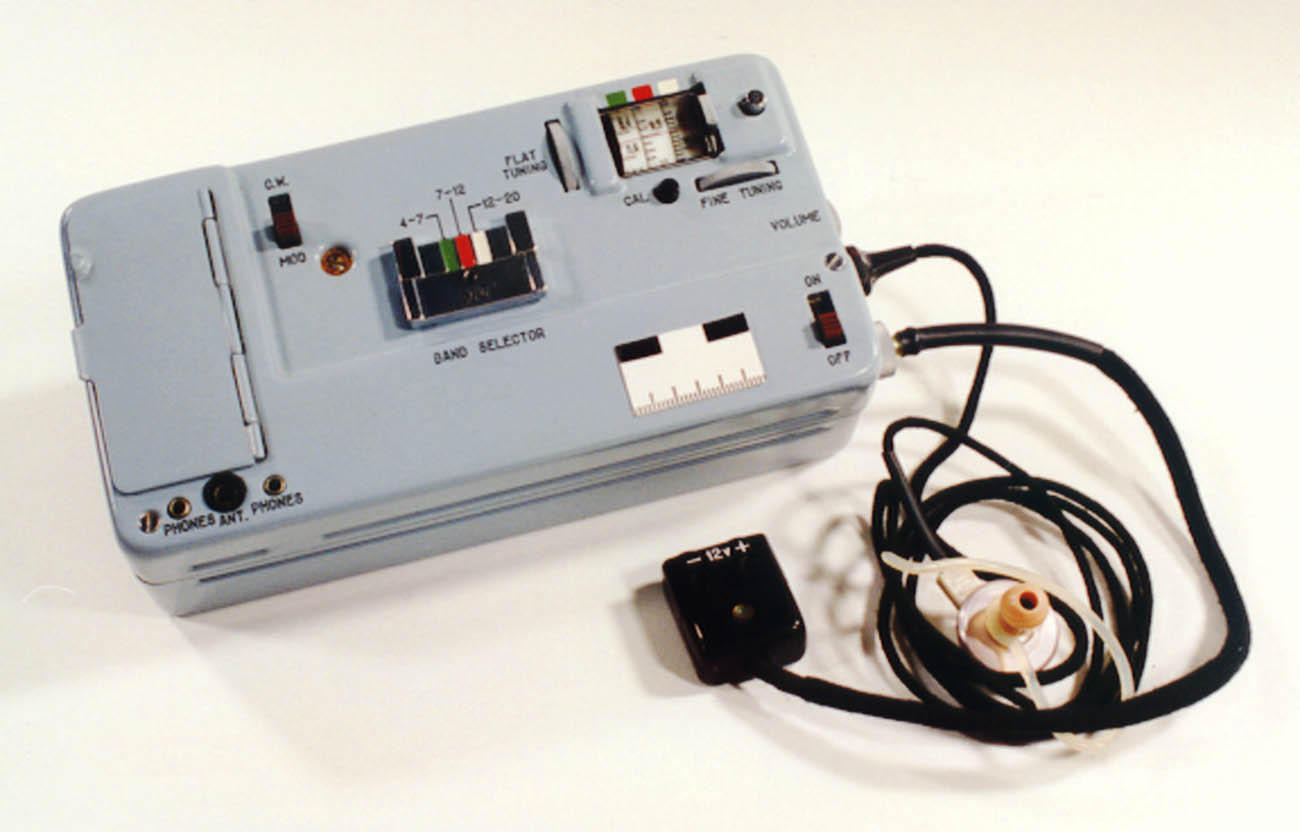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