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族住宅村的活力催化剂

在人们眼里,瑞士的农村曾经一度错落有致、生机勃勃,可如今它们当中有不少成了通勤一族的住宅新村,在为能够保持社会生活的活力而苦苦挣扎。不过,往往只要有一个人努力,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门前点缀着木制长凳的古老农宅,以前曾是首都伯尔尼西郊苏巴尔格村(Suberg)随处可见的一景。夜幕降临,疲倦的农民会坐在长凳上休息,过往邻居则会驻足闲聊一阵儿。
然而,这样的日子已成过去。藏在灌木丛后的摩登别墅现在已经取代了大多数农庄,乡间的慢车道也让位给高速铁轨与高速公路。
“你再也见不到有谁会面街而坐了,”苏巴尔格村人卡特琳·格施文德(Kathrin Gschwend)说道:“现在家家有的都是后花园。”
这几十年来,为了迎合那些为生活在城市奔波、但想拥有一座安静家园的居民,苏巴尔格村和许多其它瑞士村庄一样,变成了所谓的“住宅新村”(Schlafdörfer),虽有大量宽敞的别墅,却几乎没有社区的感觉。
在只有612位居民的苏巴尔格村,当地小店儿、邮局、鼓乐队和农民合作社,都已是尘封往事。如今的居民去附近的镇子购物、在邻近的城市上班,平时也很少跟邻居来往。
“这里晚上幽静得出奇,”西蒙·鲍曼(Simon Baumann)抱怨道。他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几年前跟伴侣格施文德一起搬回家乡居住。在这儿体会到的孤独感令这对年轻人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不久前拍了一部纪录片反映这座村庄的变化,得到的反应却让他们感到惊讶。
在苏巴尔格村出生长大的制片人西蒙·鲍曼,同他的伴侣格施文德一起摄制了纪录片《以苏巴尔格村为例》。影片以诙谐感人的手法,讲述了鲍曼在搬回家中的老式农宅后,试图融入村庄生活的经历。他不但加入了村里的男子合唱团,还去敲响左邻右舍的家门,就为了多认识些人。
多年前,他叔叔曾用超8毫米胶片拍摄过家庭录像,布满颗粒质感的画面展示了小村子在他爷爷那个时代的生活片断。他的爷爷-一位勤劳的农民-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过世,他的葬礼游行是村里举行的最后一次,这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以苏巴尔格村为例》在尼翁(Nyon)的2013届国际纪录片电影节(Visions du Réel)上首映,并赢得奖项。鲍曼还获得了去年10月伯尔尼州电影奖的最佳导演奖。
该片于今冬在德语区各影院上映,DVD将在今春发行。
影片触动心弦
今年冬天,随着纪录片《以苏巴尔格村为例》(Zum Beispiel Suberg)在瑞士德语区各影院的上映,鲍曼与格施文德收到数百封观众来函,诉说他们的村庄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令他们觉得心痛。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信件,”鲍曼吐露:“似乎到处都在上演苏巴尔格村的故事。”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鲍曼自己的经历。他的童年好友都已离开苏巴尔格村,去苏黎世或者伯尔尼谋求发展。因此他参加了村里仅存的俱乐部-男子合唱团,想要结识些当地人。可就连这个主要由退休老人组成的合唱团也面临危机-除了鲍曼外,合唱团再也招收不到新的成员。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城市与地区规划教授马丁·舒勒(Martin Schuler)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舒勒称,曾经起到联络村民的当地的俱乐部与传统协会,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于老年居民。许多其它的俱乐部都因缺乏关注而逐渐消失:年轻人多迁入城市,而选择来这儿居住的人又有其它更重要的事可做。
“新居民的到来只是因为他们的公寓在这儿,”舒勒指出:“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而言,社区生活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新居民追求的只是方便。去大型中心城市近郊的农村居住,不但能让家庭以合理价格购买或租住较大房屋,还可以不必在上下班途中花费太多时间。对苏巴尔格村的居民来说,乘火车去伯尔尼和比尔(Biel)都只需要20分钟。
但舒勒也指出,即使小村子有了新居民,小规模的服务设施,比如村庄邮局或乡村学校,近十来年也都相继关门,让位给服务于整片地区的大型相关设施。据舒勒透露,这也可能加快了社区感消失的步伐。
地域认同感
梅瑟提到,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在村里创办和运营各种活动,那么,这种意愿这就会有益于社区感的保持。但普遍趋势却是,人们大都不愿承担义务。
“我们从扮演主动角色退到了扮演客户的角色,”他补充说,人们更倾向于参加已存在的俱乐部,而不愿创办新组织,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得开车去其它地方寻找这类俱乐部。
“人们不再对村子有认同感了,”格施文德也发出这样的共鸣。她注意到,苏巴尔格村不能为村民提供文化吸引力。“如果你对你所住的村子没有认同感,那么也不会参与其中。”
但她相信,个人主动性可以带来改变。在她跟鲍曼收到的信中,有一封来自附近齐格尔里德村(Ziegelried)的一位观众,信中解释了当地居民如何每年组织4次聚会,在杯盏交错间互拉家常。
鲍曼也有类似的想法,来重振家乡的生机。村里已邀请他加入村委会的文体委员会,鲍曼计划跟他们一起举办各种活动,比如露天影院,把村里人聚在一起。他拍的电影也令同村居民开始思考,所以他很乐观,相信苏巴尔格村会越变越好。
毕竟,正如他的女友格施文德所说,“住在死气沉沉的地方真没意思。”
主动的努力
弗里堡州(Fribourg)村庄阿夫里(Avry)也跟苏巴尔格村一样,几十年前那里的农舍也一座座消失,把地方腾给一栋栋住宅,里面住的大都是去村外上班的人。但身为洛桑理工空间规划研究生的当地居民马克·安东尼·梅瑟(Marc Antoine Messer),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差异。
“这儿的各种俱乐部和协会非常活跃,”这位博士生透露,他住的村子总人口大约为1800人。
单单一个室内曲棍球俱乐部,成立不过9年,活跃成员就有200人左右。

这个俱乐部每周训练两次,训练场地是当地高中的现代化体育馆。在最近的一个周一晚上,一群当地少年正在做热身运动,俱乐部主席米歇尔·穆勒(Michel Müller)在一旁默默观看。
穆勒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5年,他说:“我们也曾有过邮局、火车站,甚至还有位有空停下来跟我们聊天的邮递员。我们村要算幸运的,因为还有家购物中心,但跟过去相比,已经不再是一回事了。”
穆勒在瓦莱州(Valais)长大,现在伯尔尼工作,他初办体育俱乐部时,还只有两队年轻队员。从那以后,俱乐部不断成长,队员年龄也扩大为从儿童到成人的各个年龄段。他承认,这个村子也变成了住宅新村,但他把帮助自己和家人融入当地生活的功劳归给了这间俱乐部。
“我由此认识了村里的许多人,”穆勒表示。他决定搬到阿夫里的原因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就是看中了村子的地理位置-旁边就有高速公路,开车去伯尔尼的路途也不远。
这个村子既没有集会中心,又没有当地餐馆,所以曲棍球俱乐部充当了必不可少的集会点。
“家长们一道去给联赛助阵,”他解释说:“在这儿的聚会不同于他们在子女学校的碰面。”
家庭轿车的普及和交通设施的发展,令那些追求更安全、更宽敞生活空间的人可以迁出城市,而上下班也只需作相对较短的通勤。因而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起,大型中心城市附近的小社区就一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居民。
“这是中产阶级盖(市郊)小型住宅的黄金时期,”洛桑理工教授马丁·舒勒解释说。
随着别墅群与现代化道路的修建,农业用地在不断减少,有关部门公布,耕地正以每秒近1平方米的速度消失。举例来说,在苏巴尔格村的全盛时期,曾有过14座农场,现在只剩下两座。
尽管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瑞士,但据研究员马克·安东尼·梅瑟解释,发生在瑞士的变化却比美国等其它工业化国家晚了20年左右。当中产阶级家庭迁至农村后,城市失去了大量人口。现在瑞士城市又开始吸引到新的居民,这还是自上世纪60年代后首次出现人口回流。
不过,根据联邦统计局和联邦国土开发局的数据,2005年瑞士劳动人口中,约有63%的人要离开所居住社区去上班。
(来源:联邦统计局和联邦国土开发局)
(翻译:小雷)

符合JTI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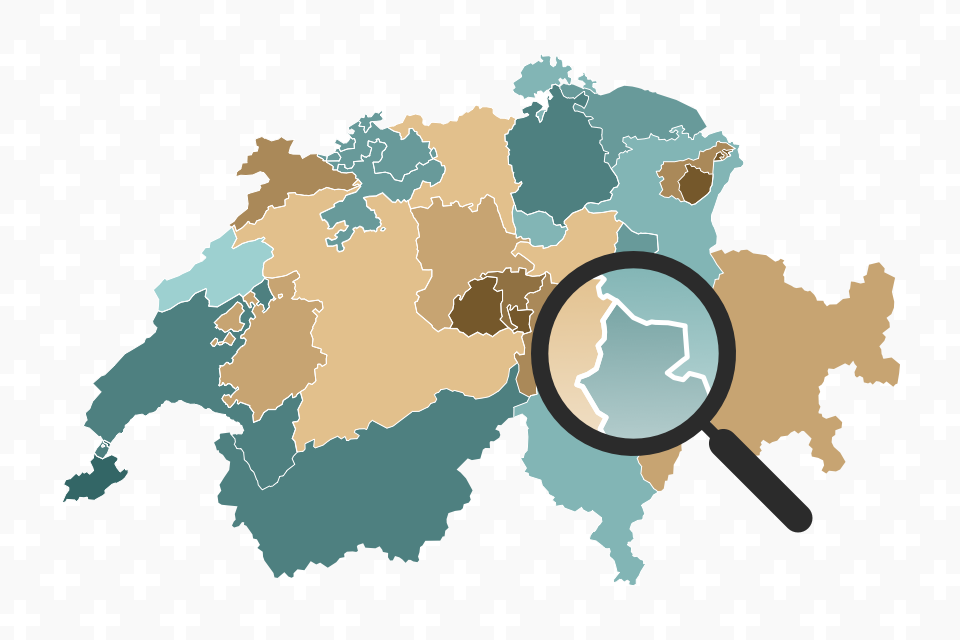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