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來自東方的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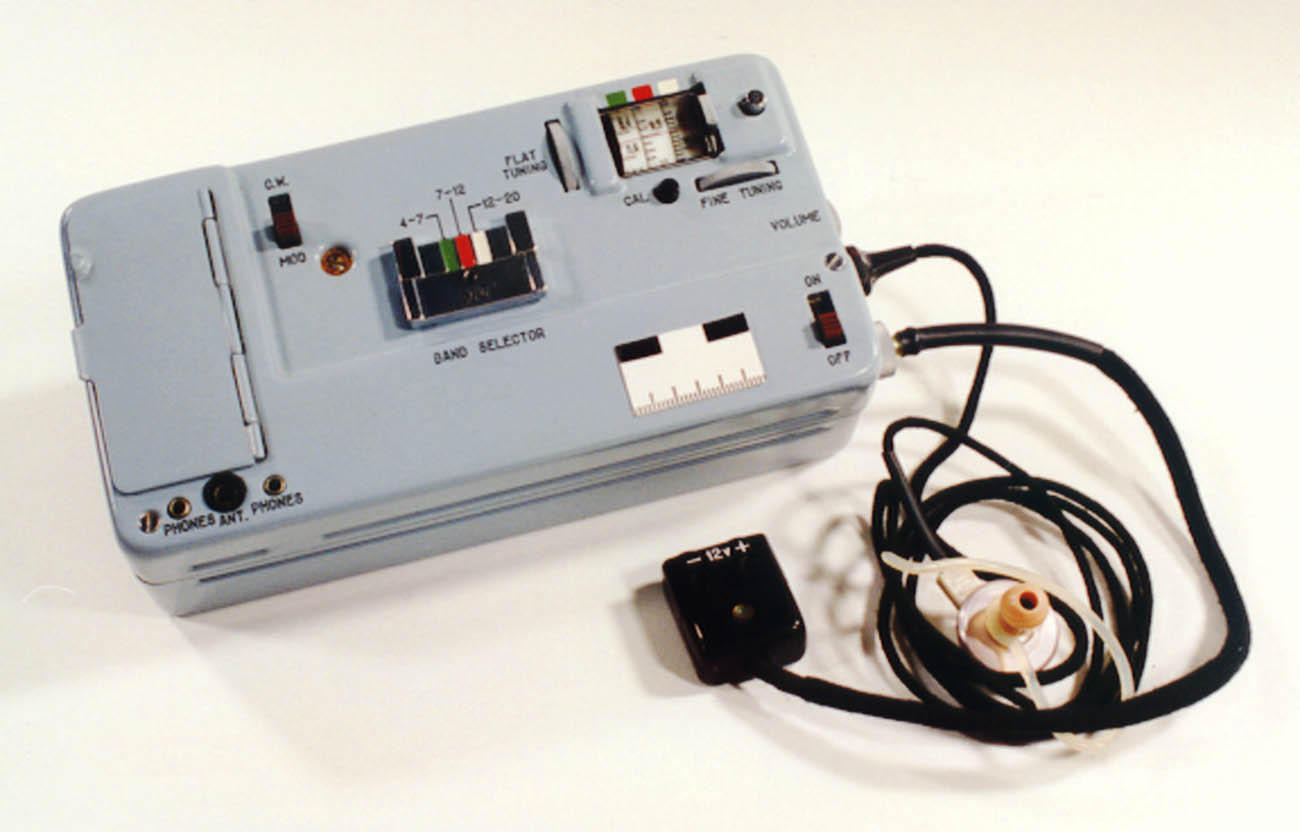
在瑞士冷戰是發生在人們頭腦中的,整個國家瀰漫著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恐懼。凡是沒有與之嚴格劃分界限的,都值得懷疑。人們堅信,敵人就藏在隔壁,還在放毒。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1956年11月,蘇聯的坦克駛入匈牙利,為了將那裡的民主革命消滅於萌芽狀態。數十萬人開始逃亡,許多進入了瑞士。這些匈牙利難民(德)在瑞士受到了極為熱情的款待,其熱烈程度人們在二戰時和二戰後都不曾遇見。因為這些匈牙利人不僅是受難的民眾,更是瑞士在反共鬥爭中的兄弟姐妹。
本文是我們的系列文章《冷戰中的瑞士》的序曲。歷史學家David Eugster從不同角度勾勒出當時的瑞士,是如何中立地位列兩大陣營之間,又明確地歸屬於西方的。
與此同時,其所引發的怒火也燒到了與共產主義帝國-蘇聯可能有聯繫的所有人身上。瑞士的共產主義政黨“勞動黨”(PdA)被當作是“外國的黨”遭到唾罵,其黨員也被稱為國家內部的敵人。他們的商店被攻擊、一些人被解僱,還有些人直接受到了暴力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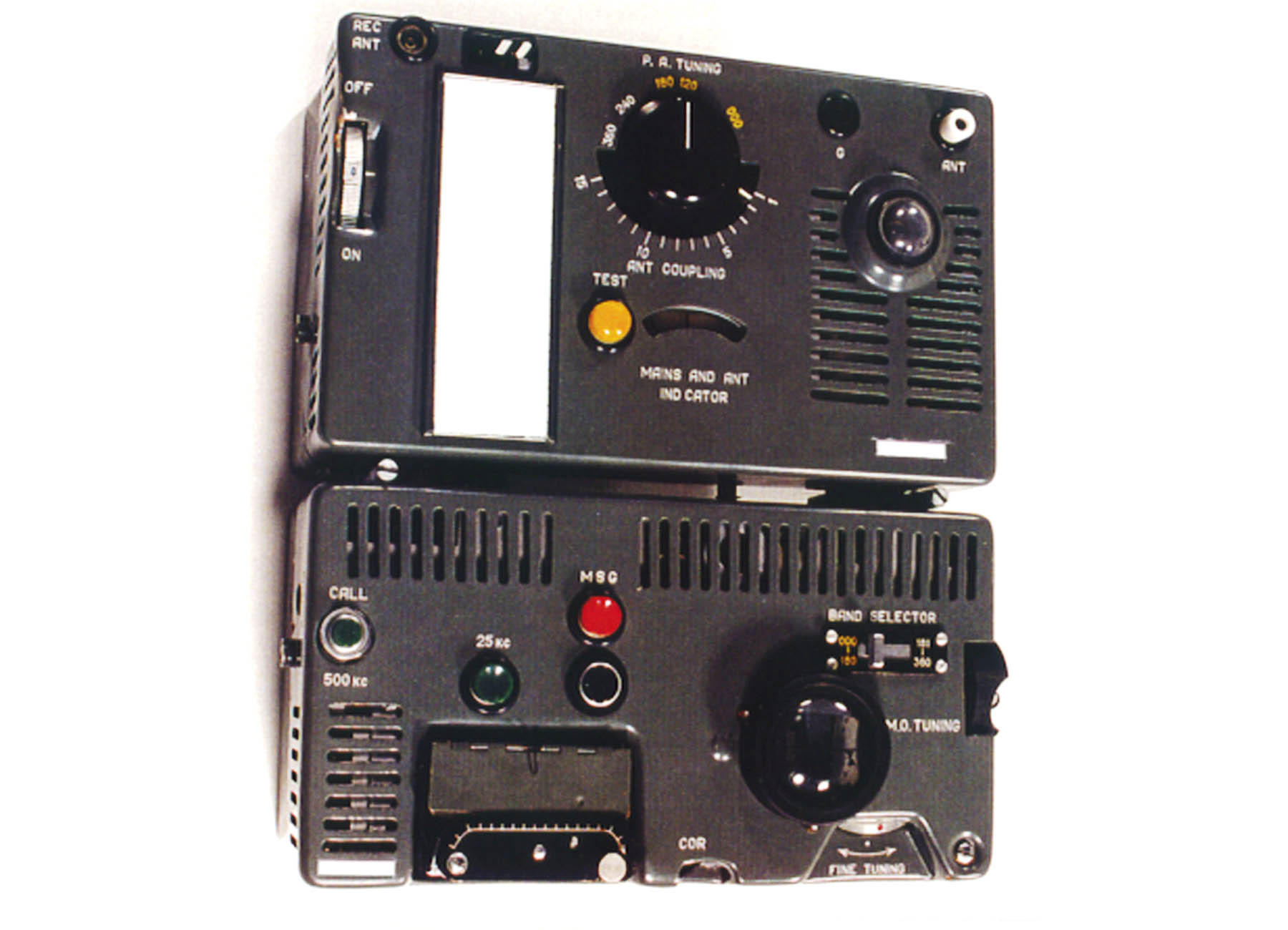
站隊之舞
強烈的反共情緒激起了蘇聯更富有攻擊性的對外政策。可惜瑞士勞動黨並不擅長與史達林所領導的暴力社會主義政權劃清界線-二戰後史達林對所有的政治力量進行了大清洗。瑞士的反共浪潮逾越了民主批評的界限而陷入狂熱。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將“冷戰中的反共行為”稱為“瑞士的站隊之舞”。
瑞士要跳給世界舞台看:1945年後,瑞士陷入孤立境地,因為戰爭中它所扮演的中立角色受到了戰勝國的質疑。所以瑞士官方要更努力地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如此熱衷於反共,也可以轉移注意力,讓人們不必再談論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擔當的角色。迪倫馬特說:“因為我們不是戰爭英雄,所以我們至少也要當一當冷戰的英雄”。

洗腦-對心理戰的恐懼
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被當作是必須剷除的惡魔,還因為這個敵人看不見、摸不著。雖然從地理位置上講,這個敵人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亞,但它就像《新約》中的魔王一樣讓人難以捉摸,因而它也就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一種廣泛流傳令人恐懼的說法是:俄國人掌握了一種技術,可以鑽到人的腦子或靈魂裡,讓人意志薄弱、毫無抵抗能力。在瑞士受人歡迎的一本雜誌《瑞士畫報》(Schweizer Illustrierten)於1956年報導了一個案例,6位俄羅斯的不同政見人士說,在被灌入某種藥物後,人會完全喪失個人意志,讓他們從窗子跳出去,他們也會毫不猶豫。文章的結論是:“凡是俄國人暗中插手的事,不要以為它太陰森可怖了就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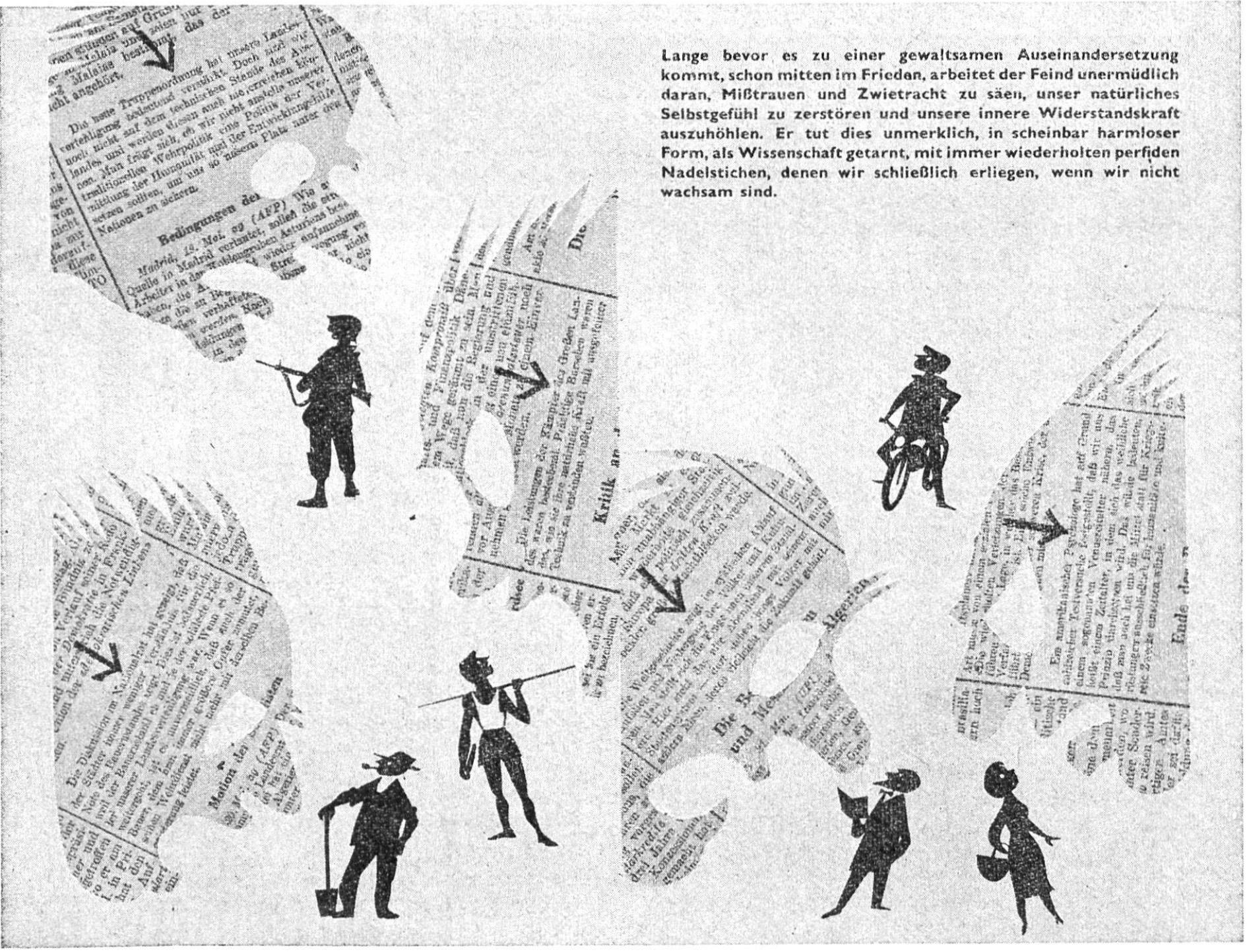
讓民眾保持清醒-還要監視
一些組織因此認為,他們的責任就是要讓公眾免於被蘇維埃無孔不入的宣傳攻勢所“麻醉”。二戰時曾以道德動員反法西斯為己任的小團體,在戰後又發現了新的工作領域:反對共產主義。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瑞士宣講服務機構(Schweizerische Aufklärungsdienst,簡稱:SAD),它於1947年成立,是前國家宣傳機關私有化的產物。 SAD成員在瑞士全境通過演講、會議等形式,就共產主義所能帶來的危險進行宣講,並經常得到國家的資助。
新聞工作者Jean-Rudolf von Salis在60年代初寫到,這裡瀰漫著一種反對共產主義的心理恐懼:“有些人,即使在人畜無害的消費合作社裡,也能嗅到布爾什維克的陰謀氣息。 ”以這種角度看,批評家就是潛在的“煽動者”,想通過秘密運作搞垮國家機構;而所謂的和平主義者,不過是想削減瑞士軍隊的戰鬥力;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會削弱打擊惡勢力的道德力量;所有的左翼中間派,均被懷疑是在瓦解瑞士的防禦能力。就這樣,反共成為了一種可以將針對國家、軍隊和祖國的批評之聲邊緣化的有效工具。

將共產主義和所有看上去相似的意識形態妖魔化,這讓瑞士的體系在一點上越來越像它的東方鄰居:開始實行全面監視。冷戰結束後人們才知道,瑞士的秘密警察和警察曾經“如何努力”地記錄並監視著假想中可能會引發政治分化的行動。隨著1989年Fichen醜聞(德) 大白於天下的,是警察機關曾將近70萬民眾的政治可疑行為記錄在案。其關注點不僅是共產黨員,還包括所有對主流社會持批評態度的,如:各種左翼、綠黨、另類、第三世界積極分子和女權主義者等。
然而直到東部(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反共的浪潮也沒有真正停止。一些如1957年成立的“為了自由”(Pro Libertate)等反共組織,試圖換一個新的目標定位:消除世界分化。人們不再談論共產主義而是講“政治正確”。他們的論戰也不再圍繞具有威脅性的世界革命,而是反對跨國組織如聯合國和歐盟。反共恐懼心理的靶心也於1989年從莫斯科轉移到了布魯塞爾。
(翻译:宋婷)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