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来自东方的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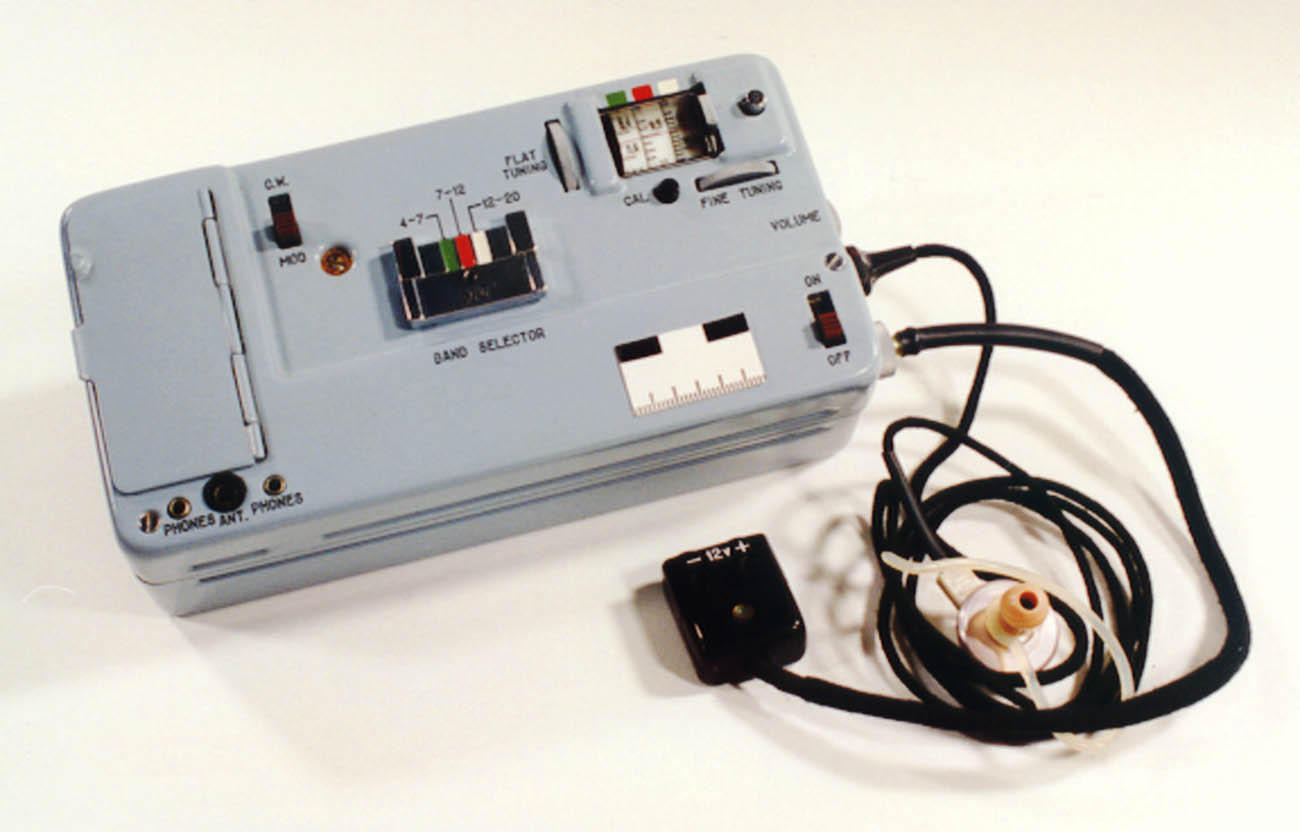
在瑞士冷战是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整个国家弥漫着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恐惧。凡是没有与之严格划分界限的,都值得怀疑。人们坚信,敌人就藏在隔壁,还在放毒。
閱讀本文繁體字版本請 點擊此處
1956年11月,苏联的坦克驶入匈牙利,为了将那里的民主革命消灭于萌芽状态。数十万人开始逃亡,许多进入了瑞士。这些匈牙利难民(德)在瑞士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款待,其热烈程度人们在二战时和二战后都不曾遇见。因为这些匈牙利人不仅是受难的民众,更是瑞士在反共斗争中的兄弟姐妹。
本文是我们的系列文章《冷战中的瑞士》的序曲。历史学家David Eugster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当时的瑞士,是如何中立地位列两大阵营之间,又明确地归属于西方的。
与此同时,其所引发的怒火也烧到了与共产主义帝国-苏联可能有联系的所有人身上。瑞士的共产主义政党“劳动党”(PdA)被当作是“外国的党”遭到唾骂,其党员也被称为国家内部的敌人。他们的商店被攻击、一些人被解雇,还有些人直接受到了暴力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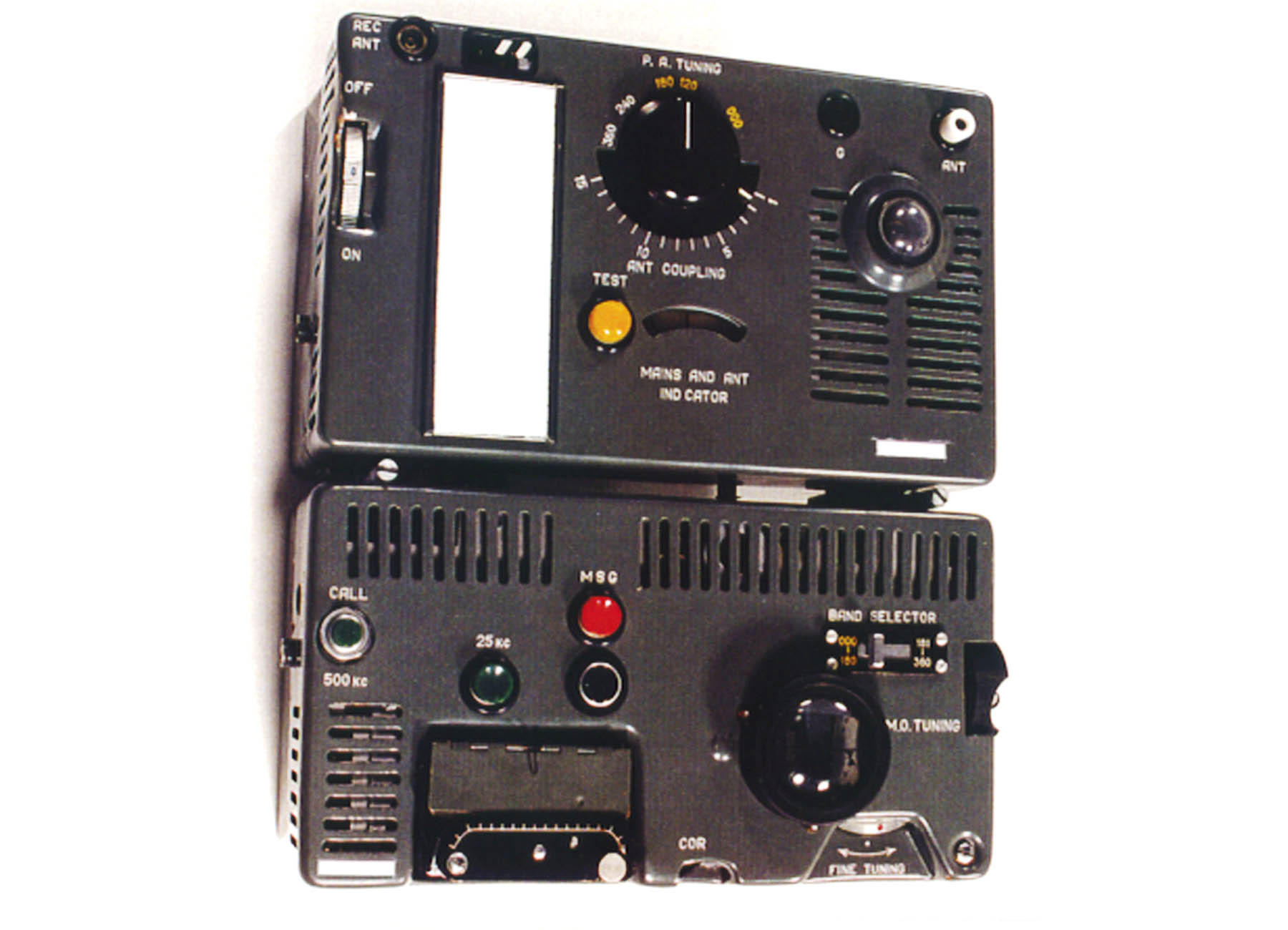
站队之舞
强烈的反共情绪激起了苏联更富有攻击性的对外政策。可惜瑞士劳动党并不擅长与斯大林所领导的暴力社会主义政权划清界线-二战后斯大林对所有的政治力量进行了大清洗。瑞士的反共浪潮逾越了民主批评的界限而陷入狂热。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将“冷战中的反共行为”称为“瑞士的站队之舞”。
瑞士要跳给世界舞台看:1945年后,瑞士陷入孤立境地,因为战争中它所扮演的中立角色受到了战胜国的质疑。所以瑞士官方要更努力地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如此热衷于反共,也可以转移注意力,让人们不必再谈论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担当的角色。迪伦马特说:“因为我们不是战争英雄,所以我们至少也要当一当冷战的英雄”。

洗脑-对心理战的恐惧
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当作是必须铲除的恶魔,还因为这个敌人看不见、摸不着。虽然从地理位置上讲,这个敌人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但它就像《新约》中的魔王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因而它也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一种广泛流传令人恐惧的说法是:俄国人掌握了一种技术,可以钻到人的脑子或灵魂里,让人意志薄弱、毫无抵抗能力。在瑞士受人欢迎的一本杂志《瑞士画报》(Schweizer Illustrierten)于1956年报道了一个案例,6位俄罗斯的不同政见人士说,在被灌入某种药物后,人会完全丧失个人意志,让他们从窗子跳出去,他们也会毫不犹豫。文章的结论是:“凡是俄国人暗中插手的事,不要以为它太阴森可怖了就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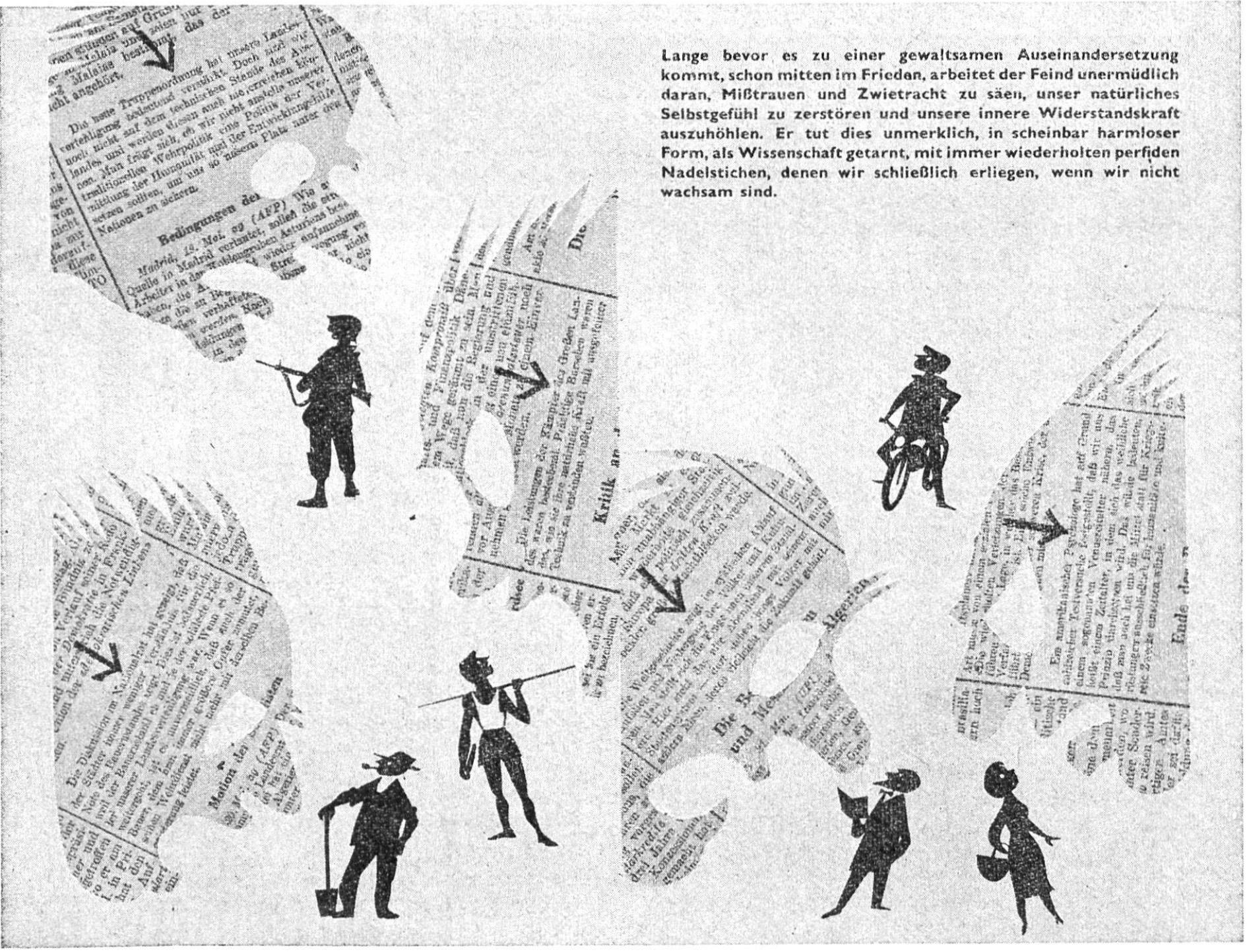
让民众保持清醒-还要监视
一些组织因此认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公众免于被苏维埃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所“麻醉”。二战时曾以道德动员反法西斯为己任的小团体,在战后又发现了新的工作领域:反对共产主义。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瑞士宣讲服务机构(Schweizerische Aufklärungsdienst,简称:SAD),它于1947年成立,是前国家宣传机关私有化的产物。SAD成员在瑞士全境通过演讲、会议等形式,就共产主义所能带来的危险进行宣讲,并经常得到国家的资助。
新闻工作者Jean-Rudolf von Salis在60年代初写到,这里弥漫着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心理恐惧:“有些人,即使在人畜无害的消费合作社里,也能嗅到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气息。”以这种角度看,批评家就是潜在的“煽动者”,想通过秘密运作搞垮国家机构;而所谓的和平主义者,不过是想削减瑞士军队的战斗力;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能会削弱打击恶势力的道德力量;所有的左翼中间派,均被怀疑是在瓦解瑞士的防御能力。就这样,反共成为了一种可以将针对国家、军队和祖国的批评之声边缘化的有效工具。

将共产主义和所有看上去相似的意识形态妖魔化,这让瑞士的体系在一点上越来越像它的东方邻居:开始实行全面监视。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瑞士的秘密警察和警察曾经“如何努力”地记录并监视着假想中可能会引发政治分化的行动。随着1989年Fichen丑闻(德) 大白于天下的,是警察机关曾将近70万民众的政治可疑行为记录在案。其关注点不仅是共产党员,还包括所有对主流社会持批评态度的,如:各种左翼、绿党、另类、第三世界积极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等。
然而直到东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反共的浪潮也没有真正停止。一些如1957年成立的“为了自由”(Pro Libertate)等反共组织,试图换一个新的目标定位:消除世界分化。人们不再谈论共产主义而是讲“政治正确”。他们的论战也不再围绕具有威胁性的世界革命,而是反对跨国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反共恐惧心理的靶心也于1989年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布鲁塞尔。
(翻译:宋婷)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