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嫁給外國人的瑞士女人會失去瑞士護照

直到1952年,與外國人結婚的瑞士女人要付出失去瑞士護照的代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 “婚姻規則”決定了數百名女性的命運。有些人死了,另一些人變成了無國籍人士,Bea Laskowski-Jäggli就是其中之一。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1945年我遇到了Wladislaw,他是Büren an der Aare拘留營中的一名囚犯。我是那裡的護士,當時歐洲仍然瀰漫著戰爭的硝煙。他於1939年加入了波蘭軍隊,不久後便淪為德國囚犯。經過三次嘗試,他終於成功地逃到了瑞士。因為會講德語,他很快就被錄用為翻譯。
戰後,他不得不去了倫敦,因為波蘭流亡政府自1940年以來一直在那裡。
我們通了好幾個月的信。然後我對自己說:‘如果你想和Wladislaw在一起,就必須去了解英國。我很快就在那裡找到了一份工作。當時,英國中產階級家庭非常喜歡僱傭瑞士的家政服務人員,於是我在1947年去了倫敦,當時我30歲。
幾個月後,換了兩份工作後,我的居留證到期了。我該怎麼辦?於是 我們說:‘好,那我們就結婚吧!看看會發生什麼’。
1947年6月,我們在朋友們的見證下結婚了。我們的家人當然都不能到場,但那一天依然是一個美好的日子!
因為與Wladislaw結婚,我失去了我的瑞士公民身份;但我也沒有得到波蘭公民身份,成了一名無國籍人士。
剛開始,許多人對我們都持謹慎態度,因為他是波蘭人,我是瑞士人,我們是都外國人。 1961年,我們都獲得了英國公民身份。從那時起,一切才好起來。 ”
“婚姻規則”

Bea Laskowski-Jäggli是1848年-1952年期間因“婚姻規則”而失去瑞士公民身份的85’200名瑞士人之一。 “而實際上,這一規則只是一項習慣規則。歷史學家和《失去的女兒們》一書的作者Silke Margherita Redolfi說:“它從未被寫入1848年和1874年的憲法或民法法典中。 ”
這一“婚姻規則”在瑞士的舊聯邦體制中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法則,在那個體制中,女性按照瑞士各州之間的協定,在婚後自動將籍貫改成其瑞士丈夫的家鄉。
同樣,當一名瑞士女性與外國人結婚時,她便自動獲得外國丈夫的國籍,這樣就能讓全家人的國籍保持一致,避免出現當時不受歡迎的雙重國籍。唯一的例外是:如果瑞士女性與一位無國籍人士結婚,那麼她則有權保留自己的公民身份。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外人
如果一個瑞士女性失去了公民身份,那麼她在瑞士的待遇就與其他外國人一樣了,因為她在二戰前曾在國外生活過,所以她在瑞士最多只能逗留三個月。如果她想在瑞士定居,則必須申請居留,通常情況下,她會得到居留證。
這些女性也無權保留自己在法律上的瑞士公民身份,因為儘管這一“婚姻規則”只是一項習慣規則,但它與其他成文法規卻具有同樣的效力“,Redolfi說。
收緊帶來的後果
戰爭期間,瑞士進一步收緊了這項“婚姻規則”。一方面,它被納入了戰爭期間生效的緊急法; 另一方面,瑞士繼續吊銷那些被納粹德國驅逐的與猶太人結婚的女性的瑞士護照,令她們因此成為無國籍人士。
而在1941年,曾出現了一絲希望,《緊急狀態法》第5條第5項規定,遇到嚴重特殊情況的女性可以再次入籍。
“許多生活在國外的猶太女性嘗試以這樣的理由申請入籍,但聯邦委員會卻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她們,”這位歷史學家說。按照聯邦的說法,只有當結婚登記處的辦事員出錯時才能使用該條款。

就這樣,一些猶太裔前瑞士女性也喪生於德國的毒氣室中。比如來自蘇黎世的Lea Berr-Bernheim,她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嫁給了一個法國人。
她和她的小兒子Alain於1944年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驅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幾個月後慘遭殺害,儘管她的家人曾與瑞士聯邦交涉請求幫助。
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了Élise Wollensack-Friedli身上。她出生在圖爾高州,因為結婚而成為德國人,並於1922年被送入一家精神病院,由於她的家鄉州在1934年拒絕了她返回瑞士的申請,她只能繼續留在精神病院,1945年她在那裡被納粹殺害。
世界大戰期間,緊急狀態法生效,家屬們面對這樣的官方決定無法做出反抗,因為聯邦法院當時毫無威力。
抵抗形成
戰爭結束後,瑞士政府試圖將緊急法轉化為正常法。因為,這一“婚姻規則”是治理移民的理想措施,從而節省了可能成為社會負擔的寡婦、孤兒或窮人的撫養費用,”Redolfi說。
數以千計女性的悲慘遭遇在社會上引發了強烈反響,女權主義協會開始行動,要求修改法律。在媒體、知名政治家和二戰期間瑞士英雄人物Henri Guisan將軍的支持下,1952年底他們成功地在議會通過了一項選擇權。

該法於1953年1月1日生效,賦予瑞士婦女能夠在民事登記處聲明保留公民身份的權力;此外,失去公民身份的女性也可以申請重新入籍。
然而,男女之間的完全平等直到1992年才得以實現。在此期間,許多家庭失去了瑞士公民身份,而受影響最大的是瑞士女性的後代。
幸福的一對
Bea Laskowski-Jäggli的生活並未因為她失去了瑞士公民身份而受到很大影響。她和Wladislaw都在倫敦西部的Central Middlesex醫院工作了許多年–她是實驗室負責人,而他是會計。他們在Ealing買了一幢房子,沒有孩子。
1953年,在 “婚姻規則”被修訂後,Laskowski-Jäggli申請了重新入籍,從而再次成為瑞士人。
Wladislaw於2006年去世,他的妻子信守承諾,再次回到瑞士生活,直到2016年去世。 “我本來不想回到巴塞爾生活,但Wladislaw認為這對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回來了。”
回來之前,她將丈夫的骨灰埋在了他家在波蘭的家族墓地中,“如果我把他留在倫敦,就不會有人管他了。在那裡我知道他會得到鮮花和他需要的一切。”
……
Bea Laskowski-Jäggli(1917-2016)的自述是受Simone Müller的《每年春天我們的女孩們都湧向倫敦》(Alljährlich im Frühjahr schwärmen unsere jungen Mädchen nach England)一書中她自己故事的啟發,Limmat出版社 。
Silke Margherita Redolfi,《失去的女兒們》,Chronos出版社。
相关内容
(譯自德文:楊旭東)

符合JTI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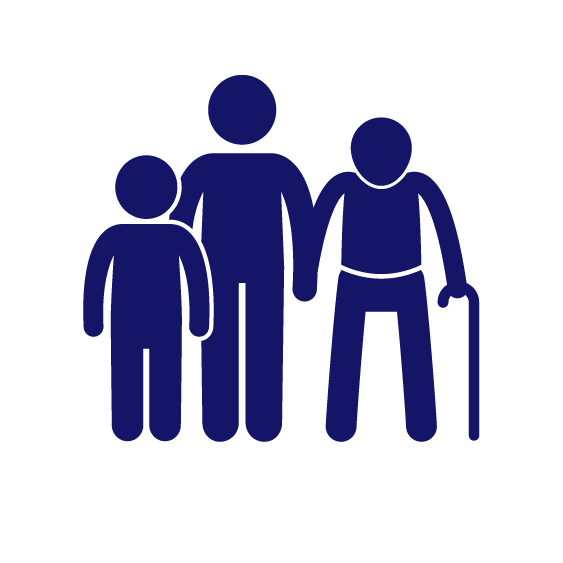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