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强制寄养制度的幸存者众生相
1981年前,不符合瑞士社会规范的无辜公民统统被送往孤儿院、监狱或拘留中心。如今,这种制度压迫下的个人肖像画连同他们的故事一起出版问世。
摄影师乔斯·施密德(Jos Schmid)拍摄的黑白照片直白地描绘了当时制度的受害者。肖像(德)外部链接之书由瑞士联邦委员会下属的独立专家委员会(IEC)委托出版,重点关注那些瑞士强制寄养制度的受害者。 该出版物共十卷,目前已出版第一卷,专门研究瑞士的历史实践。
这一制度下的数千名幸存者曾经遭到冷落、毒打甚至性侵,他们的供述(英、德)外部链接充分反映了儿时所遭遇的痛苦。他们被迫务农和从事家务,却没有任何报酬。2016年,瑞士议会批准了3亿瑞郎(约合人民币21.15亿元)的赔偿款,用于补偿幸存者曾经的无偿劳动。2014年,其中一位幸存者掀起一场索赔运动,于是政府决定出台该补偿方案。
受强制寄养制度影响的人成千上万,以下是其中六位幸存者的故事。

米歇尔·米施勒和威利·米施勒
1960年,米歇尔·米施勒(Michel Mischler)出生后不久便被瑞士政府从父母身边带走,寄养在一所福利院中,在那里他生活了十一年。教师、护工和修女经常冷落他,导致了米歇尔的发育问题(多语)外部链接。在福利院里,他饱受身体和精神虐待。他还时常被关禁闭,遭受侮辱性言语:“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人,你将一事无成。” 他的弟弟威利·米施勒(Willi Mischler)也表示:他遭受了类似的对待,其他福利院的孩子也被护工虐待,但福利院的修女否认这一说法(德)外部链接。

玛丽安·斯坦纳
玛丽安是1951年出生的非婚孩子,她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怀上了她,因此被送到别人家寄养,为寄养家庭做家务,玛丽安出生后就寄人篱下,这种成长环境给玛丽安的早期人生蒙上了阴影。后来,玛丽安的母亲结婚,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她的继父对她很冷淡,而且虐待她。曾经收留她母亲的家庭现在收养了玛丽安,但对她很不好——她母亲未婚怀孕使得玛丽安被贴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长期的侮辱导致玛丽安缺乏自尊。由于她被政府认为性行为不检点,于是被送往福利院,至今她都不明白具体怎么去的福利院(德)外部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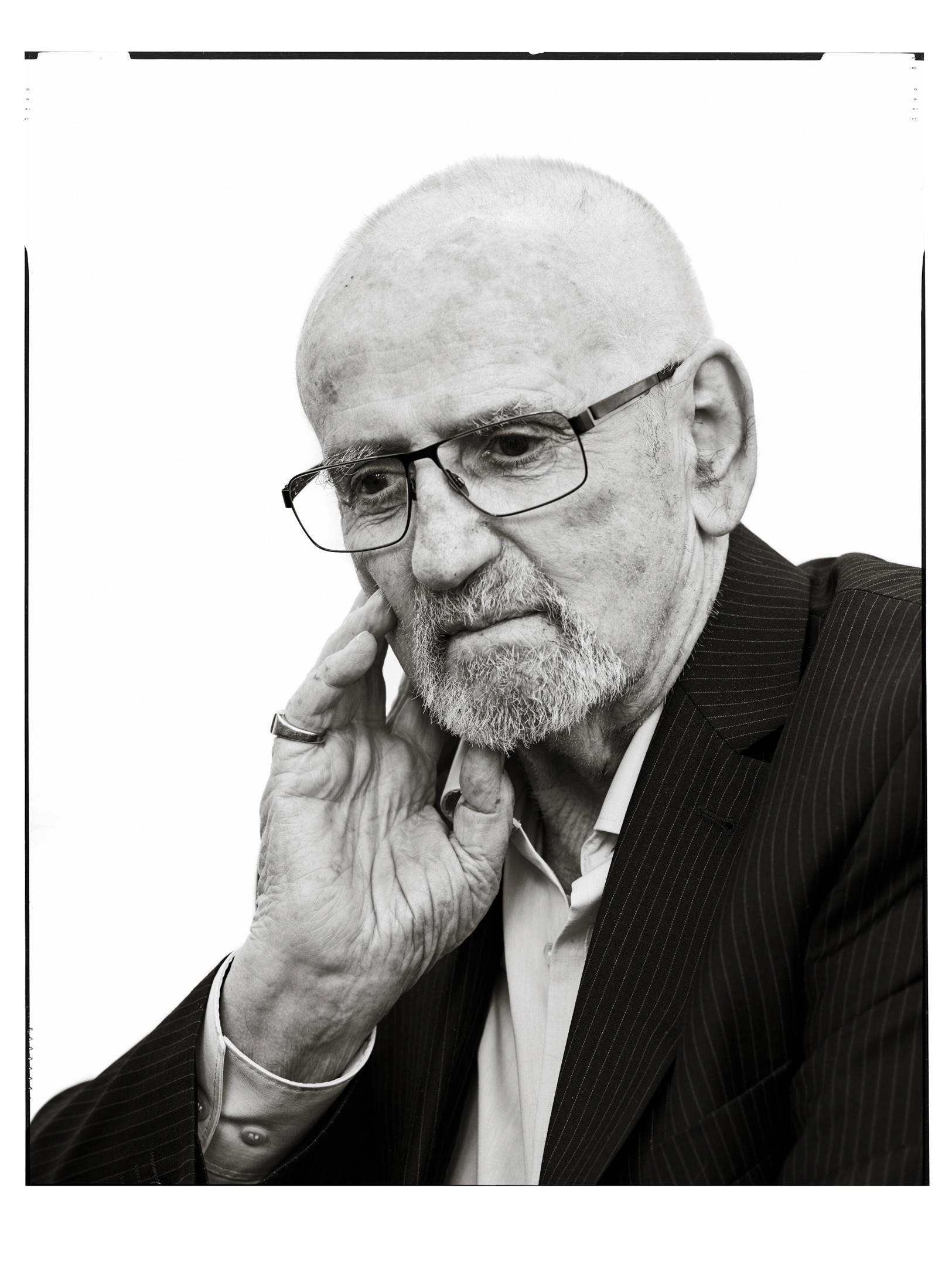
雷内·舒巴奇
雷内·舒巴奇一直大力提倡透明,他的经历促使他将自己和他人的经历记录在一本书(德)外部链接里。
“许多罪行是在教会和寄养措施的幌子下犯下的,没有人被追究责任。更不可思议的是,部分罪犯今天仍可以若无其事的生活,领取带血的养老金,毫无负罪感。 然而,羞辱、精神和身体虐待、性侵和长期劳苦却深深地伤害了当时的儿童。” 他承认那些孩子并非不可能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但他评论说,“相当多的人”去了精神病院,甚至自杀了。

米莉·库萨诺
米莉(Mili)的父母饱受二战创伤,他们经常酗酒,利用暴力来控制孩子,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在强制寄养制度下,孩子们要么被送往寄养家庭,要么被送往精神病院。14岁的米莉是唯一一个被安置在老年和严重精神疾病院的孩子。她经常是课堂上的反面教材: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坐在授课大厅的中央,教授向学生们讲课的时候用她做案例。逃到东德后,她被瑞士警方抓获并关入监狱。获释后,她决定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米莉再也没有和父母联系,凭着一份假简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她赢得了瑞士赤脚滑水冠军,并育有两个女儿。40岁时,她开始在弗里堡大学进修文化和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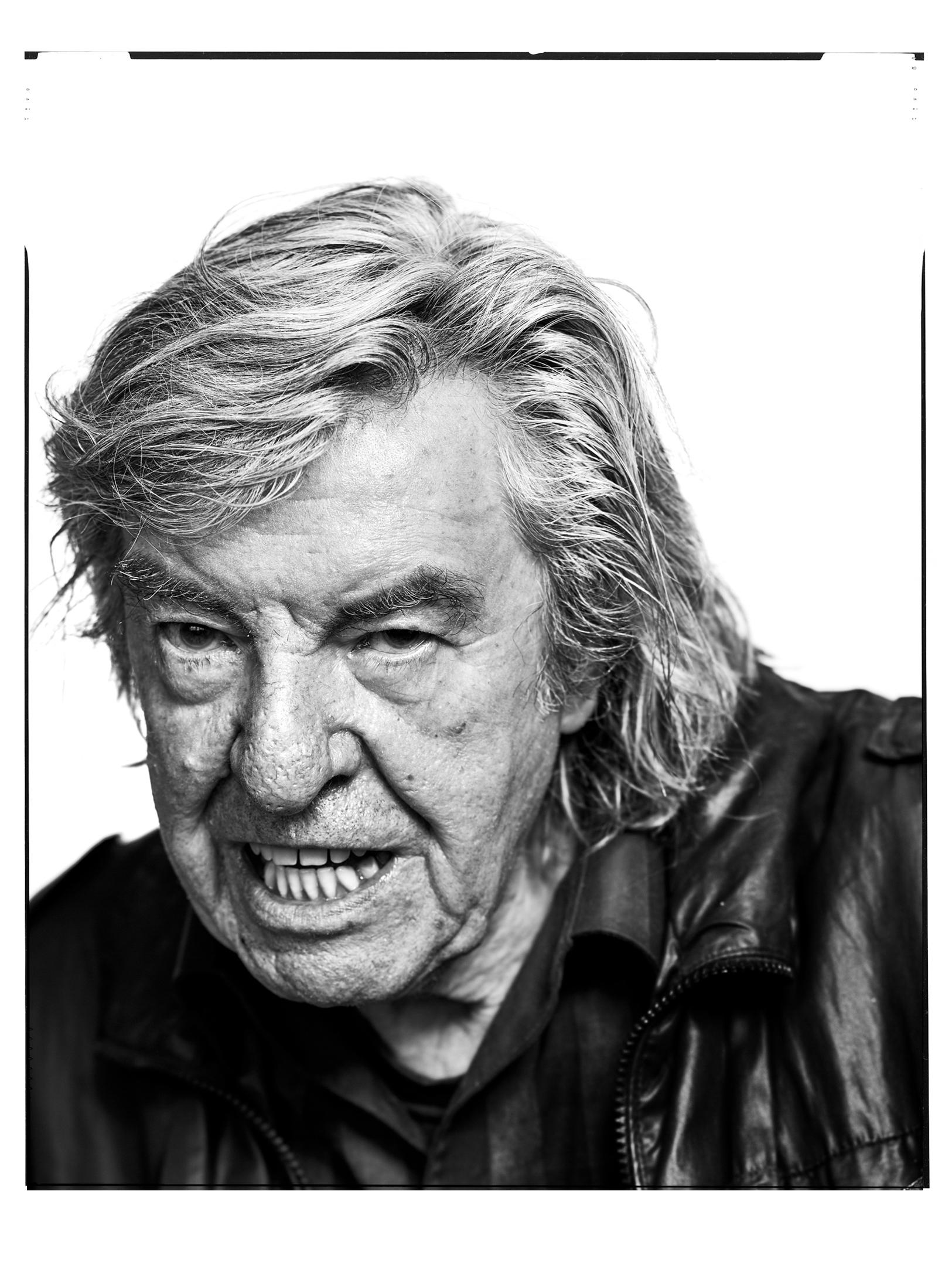
亨利·斯坦纳
1944年瑞士东北部遭到轰炸,亨利·斯坦纳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母亲在轰炸中受伤。他拒绝参加瑞士军队的基本训练,并被警察逮捕。在被强制安置于寄养机构后,他经常触犯政府规定。于是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接受了四个月的精神健康测试–最终他被认定精神正常,成功出院。他将当时的经历写成了个人回忆录《凋零的岁月》中。

玛丽娜·伯德
“它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玛丽娜·伯德(英、德)外部链接在回忆强制抚养制度时表示,“瑞士人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些苦难不仅发生在其他地方,还发生在瑞士。”
(翻译:刘烽烽)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